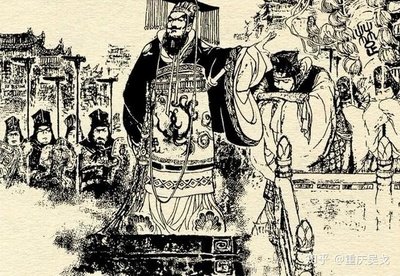
汉武帝雄才大略,在中国古代也是备受瞩目的皇帝。但根据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记载,武帝又是一个“穷兵黩武,侵伐四夷,繁刑重敛,残害百姓,极宫室之侈靡,溺神仙之虚无,去始皇亦一间耳”的皇帝。已故史学家田余庆在研读《资治通鉴》时发现,武帝晚年有“崇武”向“守文”的治国路线转变,发罪己诏,痛思己过,使汉朝免受一场亡国之祸,仍不失为一代明君。
田氏结论在各大中学生教科书里和影视作品中被广为采纳,影响甚大,几成定论。而辛德勇教授的《制造汉武帝》一书则从该观点出发,逆流而上,用侦探小说的手法在史学、经学、考古、文学等领域穿梭找寻,进行知识梳理和史料考掘、论证,深度剖析这一事件来龙去脉,最终他考证出了汉武帝现有形象的两个“制造者”:王俭和司马光。
刘宋时期的王俭,乃东晋南朝第一望族琅琊王氏之后。不过,在政治理念上,王俭对当时连年征战杀戮的扩张性国策严重不满,而主张“恭俭以济斯民”的持静守文路线。值此之故,王俭对其母武康公主参与的太子刘劭咒厌乃父的“巫蛊事件”,保有高度同情和理解态度。《南齐书》载,王俭于宋明帝时,“帝以俭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蛊事,不可以为妇姑,欲开冢离葬,俭因人自陈,密一死请,故事不行。”由此可见王俭为排遣内心愤懑,在神异故事《汉武春秋》中刻意塑造了一个“守文”的戾太子和一个晚年后悔冤杀太子的汉武帝。
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近六百年后,王俭的演绎故事被赵宋时代的司马光“别有用心”地当了真。是时,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,其所主张之富国强兵政策,与汉武帝敛财于民、用兵于外的尚武政策类似,而这却是一贯主张“以拊循百姓为先,以征伐四夷为后”的司马光所反对的。借此之故,司马光抬出汉昭帝来对比,谓“武帝作盐铁、榷酤、均输等法,天下困弊,盗贼群起,昭帝勇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,后世称明”,甚至还进一步不惜借王俭“制造”的《汉武故事》篡改历史,重塑一个晚年翻然悔悟,转向“守文”治国路线的汉武帝形象,试图以汉朝旧事作为历史,来论证其政治主张的合理性。
当然,司马光为拼凑出自己所期望的历史状态,对历史的“制造”并非止此一例。如为说明“红颜祸水”问题,他不惜借用并改编《飞燕外传》,硬是从一本市井小说里扒出史实资料;为塑造和凸显隋炀帝十恶不赦的暴君形象,他又刻意选择《大业杂记》的资料,而对《隋书·炀帝纪》与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的记载置若罔闻。
唐刘知几在论述史书功能时说:“夫史之称美者,以叙事为先。至若书功过,记善恶,文而不丽,质而非野,使人味其滋旨,怀其德音,三复忘返,百遍无斁,自非作者曰‘圣’,其孰能与于此乎?”即谓后世寻常史家撰写史书,当以如实记述史事为第一要务。司马光在编撰《资治通鉴》时的史料处理方式,确有颇多的失当之处,对于后世的读者而言,恐多有误导和不妥之处。
掩卷而思,“制造”的现象实非历史学界所独有,法学界尤其司法实践中亦常出现。君不见,近年来的各种冤假错案,如念斌案、赵作海案、佘祥林案、聂树斌案等,哪一案件沉冤昭雪前不是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的“铁案”?而在真相大白之后,哪一案件又不是个别司法人员故意“制造”事实、“制造”真相的枉法事件?对比史学领域与法学领域的这些经由臆断而制造出的“冤假错案”,我们发现,其手段与目的惊人相似,都是为一己之私而对所掌握的事实或材料进行肆意裁剪、拼接、诠释,以为我所用,其后果与影响也是异常严重。史学领域的“制造”,僭越历史真相,让后人生活在虚构的幻象中而茫然不自知;而司法实践中的“制造”更是为祸不浅,它直接以断章取义或者虚拟的事实替代法律事实和客观真相,僭越作为法治底线的公平正义,不仅污染“水流”,更是污染“水源”。
就此而言,《制造汉武帝》一书可谓一本还原历史真相的求真之作,它对我们司法实践的启示意义尤为深刻:一方面,它警示我们,在具体的司法办案中,要时刻警醒自己的居中审查身份,不偏不倚,以事实为依据,而非根据个人偏好裁剪证据材料,从而导致偏向和司法不公。另一方面,它提示我们,要立基证据的客观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,在证据材料转换为证据的过程中,时刻保有高度的警惕和合理的怀疑。因为,唯其如此,我们才能够在“大胆推理、小心求证”过程中排除非法证据,最终“拨开云雾见月明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