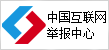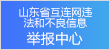董康问题:变法与循法之间

宣统二年十二月,“礼法之争”的折衷产物《钦定大清刑律》颁布,尽管迫于压力增加了维护传统纲常伦理的《暂行章程》,但基本体现了沈家本、董康等法理派“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,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”的基本立法主旨。清朝覆亡后,董康经过立法、司法和法学教研的多年历练,亲眼目睹了“纸面上的法”和“行动中的法”之间的龌龊,逐渐否定其当年的主张,试图回归传统,这种在移植西方法律过程中的退步或迂回,被学界称之为“董康问题”。
《钦定大清刑律》为世人提供了一个观察董康的视角。该法对传统礼法体系的解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方面,刑事责任上淡化体现纲常伦理的尊卑差别。传统刑法对亲属相犯的处罚贯穿着尊卑有别精神,以卑犯尊者通常加重处罚,反之以尊犯卑则减轻处罚。如故意杀人罪,《大清律例》规定,谋杀祖父母、父母、外祖父母等“尊亲属”的,一旦实施犯罪,不论是否造成伤害或死亡结果,皆斩;造成死亡后果的,皆凌迟处死。而尊长谋杀卑幼的,已经实施犯罪的,依照故意杀人罪“减二等”;造成伤害后果的,减一等;造成死亡结果的,依照故意杀人罪处罚。《钦定大清刑律》仅规定“杀尊亲属者,处死刑”;而对于以尊犯卑的犯罪,则与常人之间的杀伤犯罪同样处罚,体现出纠正伦理等级,弱化尊卑差别的平等倾向。
另一方面,厘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。传统法律礼法合一,以法律手段调整道德关系,最为典型的就是礼法之争中引发激烈争论的“无夫奸”问题,《大清律例》规定,通奸的,“杖八十,有夫者,各杖九十”;诱奸的,“无夫、有夫杖一百”;强奸的,“绞监侯;未成者,杖一百,流三千里。”《钦定大清刑律》吸收了法理派“无夫奸”等道德问题无须刑法调整的主张,除对强奸、诱奸(刁奸)等性犯罪进行规范外,仅把和有夫之妇的通奸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畴。《钦定大清刑律》表决时,礼教派和法理派经过激烈争论,最终把“无夫奸”纳入《暂行章程》。
《钦定大清刑律》颁布不久辛亥革命爆发,民国初立,百废待兴,制定法典并非易举,因此,北洋政府将封建君主专制的相关条款予以删修而成《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》(简称《暂行新刑律》),于1912年4月颁布实施,直至1928年9月被南京国民政府《中华民国刑法》取代,前后施行近17年。《暂行新刑律》使法理派通过立法改造社会,实现国家富强、民族独立的美好蓝图付诸司法实践。
早在1903年有论者提出:“新社会必新政治,新政治必新道德,新道德必新法律。”遗憾的是,在新刑律摧毁了传统纲常伦理之后,法理派所期待的新国民、新道德、新秩序不仅没有出现,还催生了一个在董康看来“今于法律不受制裁,因之青年之放纵,奸宄之鸱张,几有狂澜莫挽之势”的社会,这可能是法理派始料未及的。1914年起,董康先后任北洋政府法律编查会副会长兼署大理院院长、法制编纂馆馆长、司法总长等司法要职,其间出台或修订的《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》《刑法第一次修正案》《刑法第二次修正案》体现了向传统礼教的回归。
最为典型的是将“杀伤尊亲属”区别于常人间的普通犯罪,表现出对传统纲常伦理精神的有限继承。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《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》居然吸纳了当年礼教派的主张,不仅明确正当防卫条款“于尊亲属不宜用之”,而且把尊卑相犯差别处罚的传统做法重新纳入刑法。1915年北洋政府修订刑法,董康等人在《修正刑法草案理由书》中说明,在刑法总则中增列“亲属加重”专章,在更广的范围内恢复了宗法伦常原则。
董康还对礼法之争中“法律和道德分离”的主张进行了反思。他痛心疾首地指出,过去法律所禁止的纵欲败度行为,在如今的法律几乎不受制约,“以故青年子弟,……坠入迷途,习为奸宄,比比皆是。”董康因而认为“始信吾东方以礼教立国,决不容无端废弃,致令削足就履”。因此,对于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颁布的《中华民国刑法》主张的男女平等、礼法分离等思想,董康作为当年法理派的代表人物,居然批评该法“不顾习俗”“斫丧伦常”,反映了他试图通过礼教重塑法律权威的鲜明倾向。
如果把用法律改造社会秩序称为“变法”,把用法律来确认和维护现存秩序称为“循法”的话,在“变法”与“循法”之间一定存在某种紧张关系。“董康问题”至少提醒我们,经过100多年的大规模法律移植,只有反思我们的得与失,才能在“变法”和“循法”之间找到结合点,集聚不断前进的动力。
今日推荐山东媒体头条
Copyright © 1997-2010 SDNews.com.cn All Rights Reserved.
新闻许可:国新网3712006003号 电信许可:鲁B2-20090035 ICP:鲁ICP备09023214号 主办:山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